谢克忠:风吹过的夏天(外一篇)
发布日期:2014年07月11日
作者:谢克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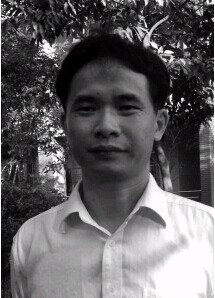
认识一个地方,就如认识一个朋友,需要缘分。
几个月前,我不知南沙旧街在哪里,甚至听也没有听过这个地名。而有一段时间,我需要每天都去拜访它,把自己当作主人,坐进厅堂,烧水、泡茶、扫地、抹桌,招呼一切应该招呼的朋友。
这样离奇的事情,发生在2013年夏初,结束在夏末。整整一个夏天,我都沐浴着海风的吹袭。记得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,她很慎重地说,借调你来帮忙,筹办一份报纸,我只给你一个月时间适应。报纸筹办处设在新闻中心,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,接受新闻中心的领导。就这样,我和南沙旧街结缘了。有时出去采访,新同事向人介绍我时,除了说清楚姓名,还要外加一个报纸的“筹办人”。这话不全对,也不全错,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
适应一个地方,比适应一个朋友更难。我用尽力气去熟悉南沙,了解南沙。早晨从榄核出发,迎着朝霞一路狂奔;傍晚,又从旧街回家,绚丽多彩的夕阳照射过来,反射在车窗上,有些迷离,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南沙是一座移动着的海滨城市。无论是公务员,还是企业的主管、经理,大都把家安在广州市区,早出晚归。每到夜间,这个城市显得特别安静。而早晚上下班高峰期,竟然拥挤的堵车。我不解地问同事,怎么会如此反常?同事笑而不答。只是神秘地回应了一句,以后你就知道了。
南沙旧街之所以旧,就是因为它作为城市发源得早,是相对于新城区金洲而言的。几条简单而狭窄的街道,显出了它的老气。高大的榕树,把一条街道掩映得荫凉无比。兴发路作为一条重要通道,沿街楼高不过四层,布满了手机店、小旅店、眼镜店、士多店、小饮食店,一个小型公交站,几台庞大的公共汽车,让这里变得局促而拥挤。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,刘副部长亲自送我来报到,第二天我自己开着车来,居然还找不到上班的地方。
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。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路上,象候鸟一样地迁徙,便向朋友的亲戚借得一间房,暂居在大岭村某民居里。房东姓罗,年龄和我相仿,生了两个男孩子。大儿子大专毕业,小儿子正在读高中。听朋友介绍,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大专生,他具有表演相声的天才,连罗俊英都称赞他是个有潜力的孩子。我听后不禁有些惋惜。在高考的指挥棒下,他肯定和我一样迷茫过、痛苦过、挣扎过。最后不得不选择屈服。人世间少了一个相声大师,多了一个网络工程师。女主人桂姐是个高大、漂亮、热情的农家妇女,都快奔五的人了,依然每天洋溢着青春的活力,跳广场舞,做健身操、干家务活,整日忙碌而充实。她说,她大儿子对计算机也很痴迷。我睡的房间就是她大儿子曾经睡过的,里面摆满了关于游戏、卡通方面的杂志。我说,那就好。一个人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,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。
早晨,推开窗户,天空瓦蓝瓦蓝。鸟的啁啾伴随着城市一起苏醒。罗氏祠堂就在眼前,建得有些像四合院,顶上盖着琉璃瓦,曲径通幽,雕梁画栋,十分气派。平常,这个大门是开的,却很少有人进去。我想到了祭祀的时候,大岭村的罗氏子孙一定都会来这里顶礼膜拜吧?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究竟有多深?这就是一个记忆的符号。中午、晚上,我每天两次走进这个“新家”,和房东夫妻俩唠家常,甚至和他们年近九旬的老母亲交谈。老奶奶耳聪目明,思维清晰,说话带有浓郁的东莞口音。尽管她的语言我只能听懂一半,我却尽量对着她微笑,侧耳细听,然后不时用半生不熟的粤语插上几句。老人很高兴和我交流,让我渐渐觉得自己不再是客人。大岭村依山起,背山面海,是个风水宝地。据说这里人才辈出,官员、老板出了不少。从村民的新房就可见端倪。一个人、一个村庄、一个城市,无论怎样变迁,总有那么一点可以追踪的记忆。
海风吹到旧街,好象已经变了味。没有办法让人想象出海的辽阔和壮美,而是透不过气来的燥热。小宜说,海风、阳光、沙滩,那是浪漫的传说。长期生活在海边,容易让你的皮肤变黑。出门的时候,你最好戴上防辐射的墨镜,不然容易得白内障。我试着把旧街走了一遍,感觉不出特色,除了拥挤和嘈杂,就是那些小店小铺。既没有现代气息,又缺乏地域特色。这里已经“旧”得让人遗弃了。地铁四号线南延段正在施工,在这里有一个地铁站。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地铁通达的地方,往往会带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。旧街,或许会成为南沙一个新的传奇。
新闻中心是南沙新闻的集散地。从主任到记者,都是活力四射的年轻人,从“七零后”到“九零后”,构成了一支生力军。走进这个大家庭,我觉得自己老了。而老是很可怕的事情,意味着淘汰。我努力地假装着年轻,从衣着到说话,从行动到思想,都显得有些意气风发,以兴奋掩饰着内心的苍凉。和这些小年轻打交道,也向他们吸取了不少精气神。
新闻中心的牌子很大,人却很少。主任阿毅,记者阿庆、老兵、小飞、小宜,播音员小关,还有一个烧饭、搞卫生的阿姨兰姐,一个开车的司机阿锋,一个搞广告的小罗。保安是保安公司委派的,三班轮,一个感应式安全门,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打开。第一天上班,保安不认识,我居然被拒之门外。以后彼此熟悉了,便像一家人一样亲密。每天早晨,同事们从家里赶到单位吃早餐。粥、粉、面、包子、面包、饺子。兰姐总是变着花样,满足这群年轻人的营养需求。中餐也同样丰盛得让人不想回家。而她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元的工资报酬。在她眼里,年轻而忙碌的文化人很崇高。她说她女儿成绩很好,凭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广东执信中学。这是一所省级名校,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考进去的,这让我肃然起敬。“王候将相宁有种乎”?
办公楼的前面是一个文化广场。每到傍晚,这里就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玩滑轮、跳广场舞、健身操,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。这和新闻中心楼内的紧张忙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寥寥几个记者,要应对803平方公里的新闻报道,采、编、播,甚至开车,个个都会。主任阿毅说,没办法啊,逼出来的!每天总有那么多事,你不做谁做?忙不过来的时候,阿毅亲自播音、制作。他们不仅要应对电视新闻,还要应对政府网站新闻、每天的手机报,在这里工作就像打仗。办公室因忙碌时常显现出杂货摊的混乱。兰姐便很耐心地清理,擦桌子、窗台,倒垃圾。叫外卖的电话很夸张地贴在醒目的位置,方便夜间加班。这群快乐而忙碌的年轻人让我肃然起敬。
短短三个月时间,报纸还没有办起来,我却要走了。领导带着十分歉疚的心情说:“真不好意思,谢谢你帮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。”我却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。这样的结局对我而言,并不算残酷,而是幸运。任何事情,只要尝试了,努力了,至于结局,并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。能尽自己的微簿之力,证明你还不是一个闲人、废人,那就够了。一个人就如木材,有的可以挑起大梁,有的只可以做门栓,你说哪个重要?临出门时,我和领导握手告别,满脸的微笑。我知道,这不仅仅是在告别一个人,而是告别一段经历,一段人生。说实在的,而今已是人到中年。儿子赴德国留学,本科毕业在即,无论是见识还是学识,都已经超过了我。能让下一代人站在你的肩膀上往上爬,那是一件无比荣光而自豪的事情。权势和金钱都是身外之物,拥有或者失去就在片刻之间, 只有内心的强大无人能敌。
离开南沙旧街一晃又是几个月。有时很想回去看一看那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,吹一吹旧街的海风,或者找一处海边农庄,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,醉倒了再抱头大睡。我想,每当我感到身心疲惫的时候,就会想起那里曾经是我人生的一个驿站,我可以把心安放进去,轻轻地抚慰,然后安然入睡。
永远的河流
鸟瞰,河流呈网状镶嵌在榄核大地,如母亲身体的血管一般细密。它们终日缓缓地流淌,无声入梦,波澜不惊。
对于没有家园的人而言,河流就是一个归宿。人类发展史,其实就是一部紧随河流的迁徙史。我们的先祖从茫茫原始森林走出来,追寻着潺潺溪流,一路奔向大海。
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。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人心。曾几何时,我就这样站立在海边,任凭海风吹拂,却找不到一条通往人心的通道。
榄核河终将流入珠江,奔向大海。日日夜夜,经久不息。它从我居住的小镇穿过,默默滋润着一个游子的思乡梦。
据史料记载,榄核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地带,数百年前这里还是洪荒泽国。先人在水里采蚝,经年累月,泥土不断堆积,终成陆地。地形如橄榄之核,故称“榄核”。我不是一个迷信传说的人(所谓的传说,其实大多是今人的杜撰,如梦呓一般)。和榄核结缘,更多是来自人民音乐家冼星海。
一个秋阳照耀的午后,几位文友相约去湴湄村。汽车行驶在田畴绿野,映入眼帘的是铺天盖地的绿色。如竹子般林立的果蔗,灿烂开放的花卉,高大婆娑的细叶榕,挺拨直立的大黄叶。干净整洁的机耕路在原野里纵横交错。友人说,冼星海就出生在这个小村。他是遗腹子,还没有来到人世间父亲就葬身大海,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。冼星海的祖祖辈辈都是疍家人,以舟楫为家,靠打渔为生。举家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。时至今日,我们在湴湄村已经找不到冼星海曾经生活的痕迹。
湴湄是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村。曾经在海上颠簸的人们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园。一条小河涌穿村而过,直通榄核河。河水清澈见底,绵长的水草碧绿透亮。河涌的两岸,建起一幢幢农家小别墅,天然形成一条小街。为纪念冼星海在海上出生,这条小街被命名为“海生街”。这个下午,湴湄显得很安详,恍如世外桃源。暖风夹着绿树和海水的气息拂面而来。作家们三三两两,沿着街道一路向北,默默走着,心情有些沉重。他们似乎是在追寻着什么,也像是在叩问着什么,小心翼翼,不敢弄出一点响声。河涌里的螃蟹在泥土里爬来爬去,筷子般长的鲫鱼欢快地穿梭,犬吠,鸡鸣。不知名的野花在路边灼然开放。长长的一条街道,在秋阳的斜射下显得很安详。走出村口,河涌立见开阔,河面上波光粼粼。偶尔可见一叶扁舟漂在水面,撑船的老大端坐船头,看见河面的漂浮物立马捞起。村口呈三叉形,数百平方的瘀泥渐成陆地。一蓬蓬粗大茁壮的芦苇,杂乱无章地疯长在河堤两旁,仅留一人通过的道路,俯首细看,原来是水泥浇筑的路面。友人说,2005年广东电视台拍摄20集电视剧《冼星海》,曾经在这个河堤取景,临时搭起了几间草屋。几年过去,草屋不见了,冼星海留给湴湄村的记忆仍然鲜活。作为一个纯粹的“无产者”,他连草屋也没有一间。一个没有家的人,四海为家,以国为家。从幼年随母走出湴湄,离开榄核,远赴澳门、新加坡,又去法国求学,他可能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他的故乡在海边,海在他的梦里,他以全部灵魂拥抱着时代,拥抱着国家。整个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。冼星海以音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狂澜。一个以国为家的人,心胸一定比海更辽阔,比天空更高远。
整整一个下午,我们沿着湴湄村的河堤漫步。或走或停,感受着冼星海的百年气息。聆听着河流的轻言细语。这河流,尤如榄核人的性格,不温不火,礼让三先,却绝不是软弱无能。面对屈辱,必然是强有力的抗争。面对死亡和绝境,必然会掀起狂飙!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榄核河,曾经哺育过冼星海。我相信,无论走到哪里,他都没有忘记故乡,没有忘记这条河。
风在吼,
马在叫,
黄河在咆哮!
黄河在咆哮!
这是发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呐喊!冼星海,这颗音乐巨星,东方红色贝多芬,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。
榄核河,还是冼星海当年的那条河。亘古不变。我们站在岸边,听着河水轻抚大地的声音,久久不想离去。
附件下载:






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0006号
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0006号



